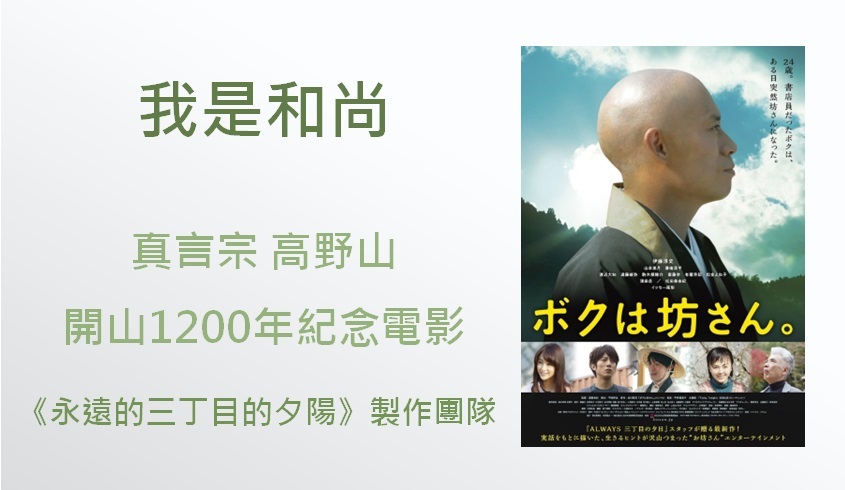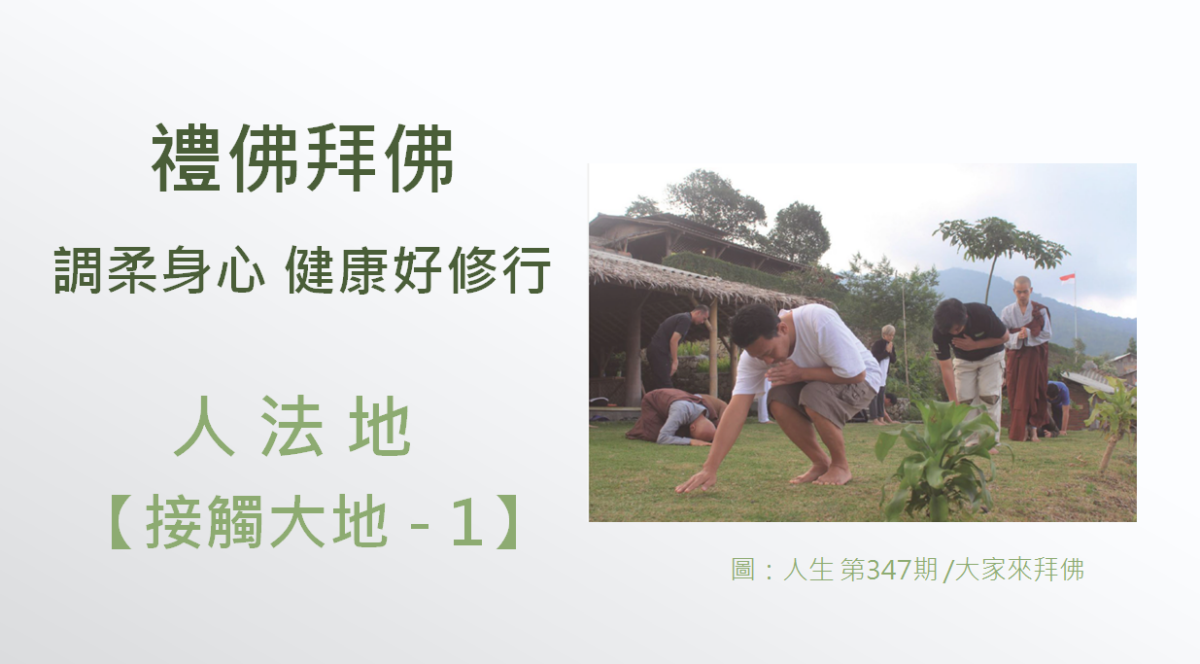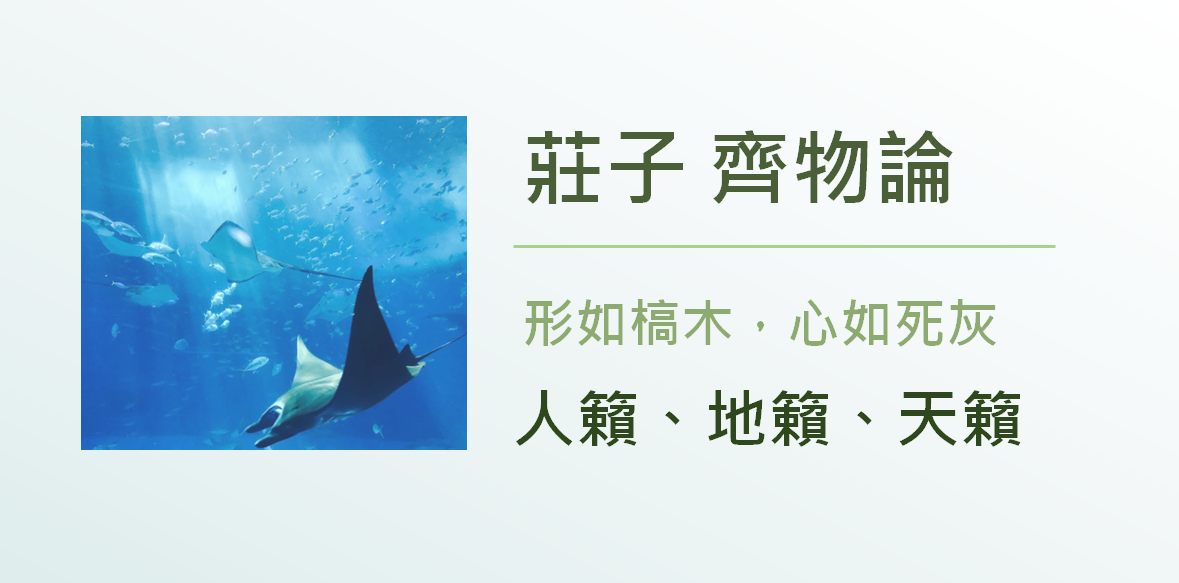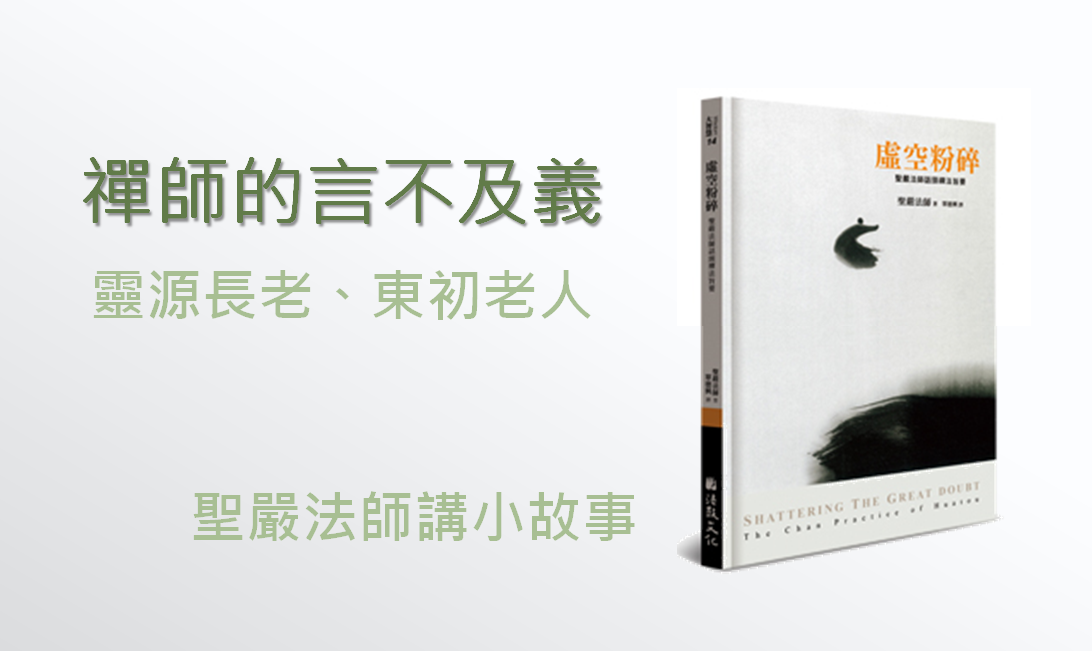日本電影《我是和尚/ボクは坊さん》
導演:真壁幸紀, 演員:伊藤淳史、山本美月、溝端淳平
2015年10月上映,改編自榮福寺住持白川密成的同名著作。
劇情傳達真言宗特色
主角白方,在就讀高野山大學、受戒取得「阿闍黎」資格後,在書局工作。由於外公驟逝,二十四歲就接任榮福寺住持,法號光圓。光圓和尚要在最短時間內扛起營運責任,在前輩及檀越長老的監督批評下,跌跌撞撞、逐漸成長為受人敬重的住持。
雖說是高野山開山1200年紀念,這部電影並不是走氣勢恢弘路線,而是藉由這位年輕住持的經歷,呈現出日本社會對和尚的期待,寺廟營運應有的風貌,以及宗教儀式與生老病死的緊密結合,傳達出真言宗的特色與入世教義。
日本佛教情形
日本的和尚(日語「坊樣」)跟我們台灣人對出家眾的理解不一樣,視之為一種職業可能更為恰當。
他們平常可以穿便服,執行佛教儀式時,如亡靈超度等才需要穿上僧服。可以吃肉喝酒娶妻、繼承寺廟的日本和尚,也有他們肩負的職業責任與壓力。
在聖嚴法師《留日見聞》文集裡有提到,日本戒律不像台灣這樣的嚴謹,近年也缺少修持精嚴的高僧。而日本社會裡還是有虔誠的學佛居士,知道日本和尚與持戒比丘的差異,很期待能夠親近真正的高僧大德。
《留日見聞》寫道:「日本僧人,可以不稱他們為比丘,不可不承認他們是和尚。請勿誤以和尚即是比丘,和尚在印度的梵話為「鄔波馱耶」(upādhyāya),譯意為親教師,不限於佛教的比丘所用,外道的在家教師也有採用的。」
有一位日本青年想信仰佛教,但日本佛教卻不能引起他深切的信心,聖嚴法師向他說:
「佛教在衰微的時代中,只要有乃至一人警覺起來,不論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,以身自許,為了挽救佛教精神生命的危亡,來做全力的自我實踐,那麼,此人即可成為一代的高僧,整個佛教的慧命,也會由於通過此人的宗教生命,而為人類帶來無限的希望和溫暖。我又進一步地告訴他,佛教的本質,不是批判主義的,乃是實踐主義的。能夠具有批評現實的知識,是好的,假如具有批評的能力而放棄批評的行為,直接以自我的實踐,來求證其所持立場之是否正確,那才是最好的。」
這段話令人感動,意即,我們應力求自己的實踐,而非去批評,才能為他人帶來無限的希望與溫暖。
對住持的期待1:主持儀式
日本人很重視儀式與祭典,不僅生老病死有宗教儀式,成年、考試、入學、就業、結婚、生產都少不了到寺廟祈福。僧侶作為宗教專職人員,被期待要圓滿引導這些儀式。
有個日本朋友聊說,他閒暇時最喜歡參與祭典,然後分享了這張照片:

老實說,一整群衣著神色都相仿的大叔,一下實在看不出他在哪裡。
不過,這種「認不出來誰是誰」,剛好就是儀式祭典最大的特色。不管原來的社會角色是甚麼,大家依神話與傳統,做一樣的打扮、一樣的表演,大家看起來都一樣。
所以在祭典中可以從平常的僵固角色解脫出來,是特別愉快輕鬆的時刻。
儀式沒有貧富貴賤
無論貴富貧賤,在儀式中都是一視同仁。傳統婚禮儀式上的新娘,也是相同裝扮。喪禮的圓滿舉行,更可以讓往生者與家屬安心。
在生命各種轉變的關卡,都有儀式與社會傳統結合,住持就是這些儀式的靈魂人物。



本站相關文章: 【佛法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