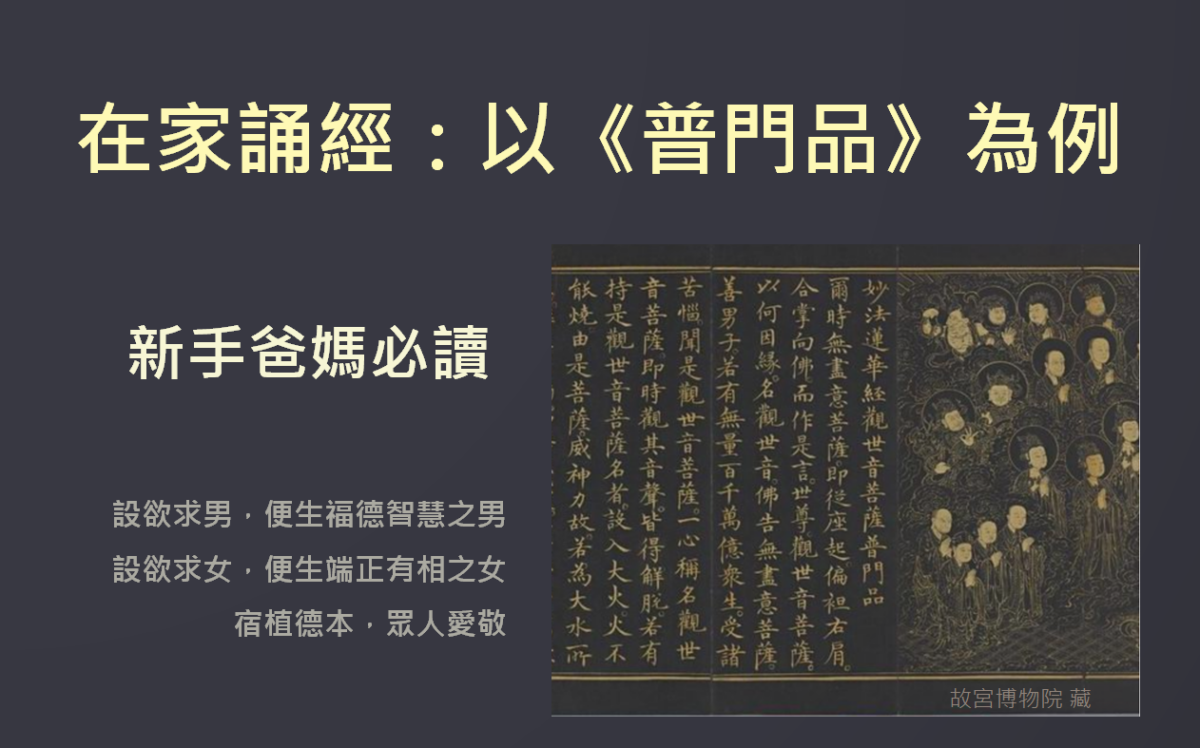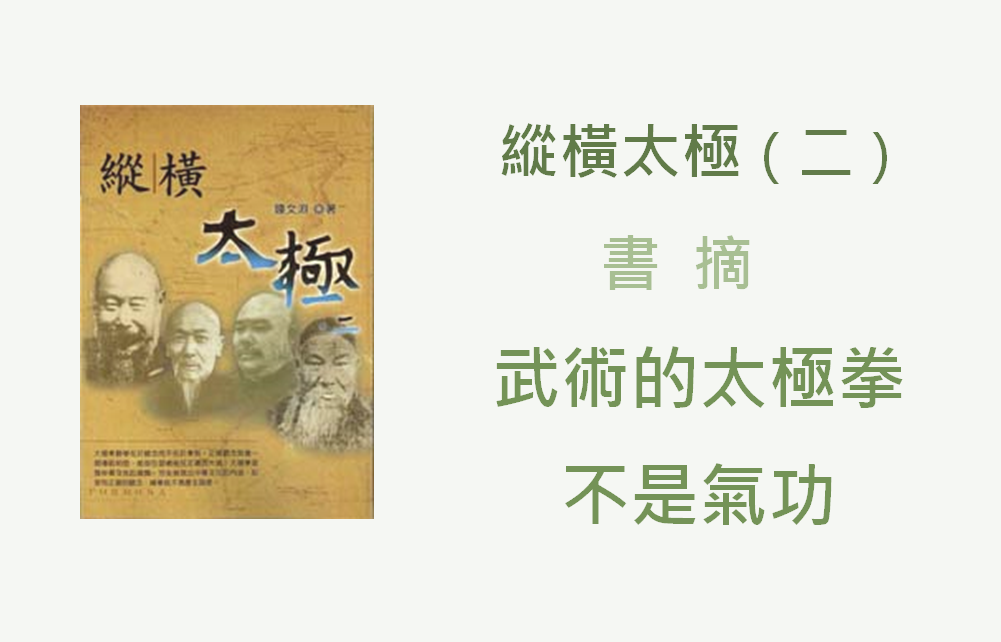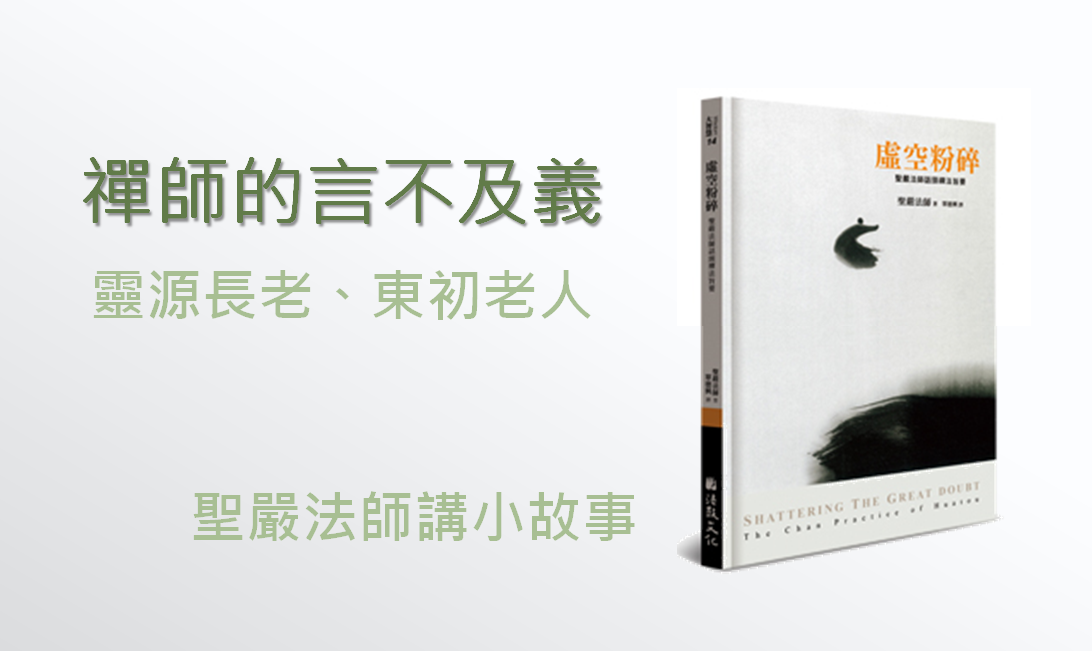在 2023/10/15 上課時,請大家就前次【道德經 心領神會01】2023/9/10 課程 中的「名可名,非常名」做實踐心得分享。一位賢者同學說了「兩種米酒」的生活小故事。
她請兒子幫忙去買米酒,交代說米酒有兩種,一種是有用食用酒精做調和的料理用米酒,另一種是全部是由米釀造的純米酒,注意要買純米酒。即使再三叮嚀,結果兒子還是買回來錯誤種類的米酒。
她本來很生氣,但忽然想到上課講「名可名,非常名」時有提醒大家,不要被「名」束縛,就忍下來沒發作。
這個小故事淺顯親切,卻富含深意。

兩種米酒一樣嗎?
兒子為什麼會買錯?因為對第一次去買米酒的兒子來說,兩種米酒是一樣的。
媽媽為什麼會生氣?因為對常在使用米酒做料理的媽媽來說,這兩種米酒是不一樣的。
可見得,能否分辨差異,跟對米酒的了解與應用程度有關,如果真的要細分,還不止兩種呢,如上圖。
每個人因著過去的經驗與學習積累狀況,決定了對事物的了解程度。
可以碰觸得到的有形事物況且如此,無形的抽象概念更是如此。
例如練武術,何謂「鬆柔」可說是一場混戰,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,而且都覺得自己很正確。
佛法也常被望文生義,例如心經的「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常被大眾拿來任意詮釋,先不論般若空義難解,就是這個「色」一詞,也是需要配合下一句「受想行識亦復如此」的「色受想行識」一整組概念合起來理解,而不能直接斷章取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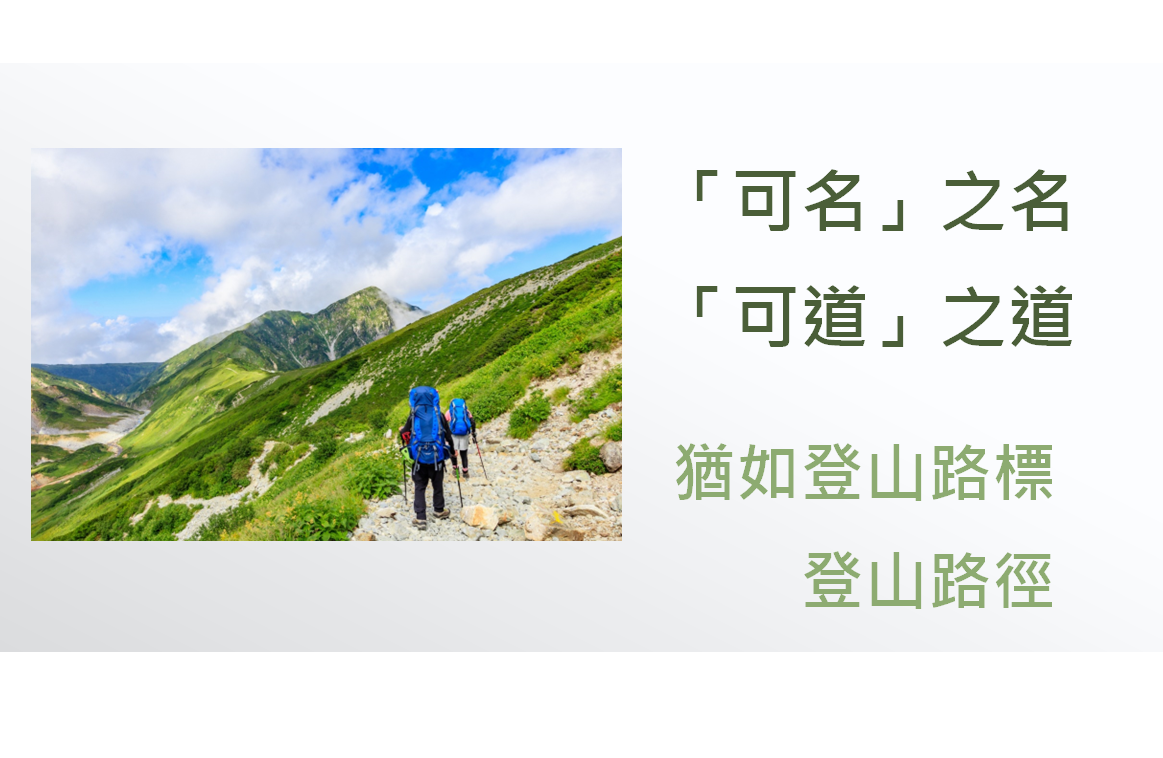
人只能分辨到自己能理解的程度
會有這種情形,是因為每個人的人生經驗不同,智慧深度不同,所以只能分辨到自己能理解的程度。
猶如爬山,每個人爬的高度不一樣,看到的清楚程度就不一樣。
已經爬三百公尺的人,看得比在地面的人清楚;但是跟已經爬一千公尺的人相較,還是不夠完整,要一直到山頂,才能將大地風光,一覽無遺。
法門理論,猶如登山路標、登山路徑
法門理論,意即「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」裡的「可名」之名,「可道」之道,猶如登山路標,登山路徑。
還沒有爬到山頂的人,所見還都有所侷限,但又不能不前進,所以需要這些相對的名稱、理論、路徑來做為路標,指引方向,等到了山頂,才不需要路標。
每個人因著不同的稟賦與環境影響,會適合不同的路徑,也就是2023/9/10 課程 裡面說的,「道」賦予萬物的「德」,沒有高下優劣對錯。
我們可以選取適合自己的路徑、路標,卻不需要去干涉別人選取的路徑。
這些理論法門作為路標,是用來輔助我們爬山,讓我們檢視、修正自己的問題,而不是用來比較、評斷別人。

盲人摸大象:相對的真實
既然人都是受自己經驗智慧所限,就不需要去評論苛責別人對事物有「錯誤」的理解,或更好的形容是「不完整、不精確」的理解。
這就像盲人摸象,每個人摸到大象不同部位,固然理解是不完整、不精確的,但畢竟摸的確實是大象,有相對的真實性。
各門派各團體既然存在,就有其發心的目標,演進的過程,及所適應的對象,只要能持守戒律,諸惡莫做、眾善奉行,不論了義與否,都值得隨喜讚嘆。
我們若不能悅納別人的見解,能不能再想想,對爬得比我們更高的人來說,我們一樣也是見解「不完整、不精確」啊。
另一方面,我們也不是每樣事物都懂,兒子可能不懂米酒的差異,但是他可會比媽媽更懂3C產品的差異。
不否定別人的存在價值
如果常駁斥他人見解為邪見、為錯誤、為不究竟,根據宇宙法則,別人也會排斥我們。
就像日蓮上人斥其他宗派為「念佛無間、禪天魔;真言亡國、律國賊」:淨土宗 – 入無間地獄;禪宗 – 天魔;真言宗 – 亡國;律宗 – 國賊,為鎌倉幕府與佛教守舊派勢力所不容,受小難不知其數,大難凡四度。 (資料參考: 日蓮 – 維基百科) 。從另一角度來說,每一宗派都有其成就因緣,或許承擔法難以能弘化,也是當時時勢所成的深刻信願選擇。
和其光,同其塵
老子身處春秋時期,是諸侯相互征伐戰爭不斷的亂世。道德經強調寵辱不驚,禍福相倚的處世觀點,有「和其光,同其塵,是謂玄同。」「知其白,守其黑。」「知其雄,守其雌。」「知其榮,守其辱。」等語。
道家風格,隱逸逍遙,不會去做引禍上身的剛強之事,不會熱衷於「破邪顯正」。
能做到和其光,同其塵,並不是忍耐或是刻意,而是對人世間有透徹了解之後,自然而為的言行表現。
這兩個禪宗小故事 「你說得對」 「有無皆是」(西堂智藏。趙州狗子),很能表現出這份放鬆。

禪宗小故事 「你說得對」
有兩個弟子在爭論,其中一個說:「師父講,人有佛性,貓狗沒有。」
另一個則說:「不可能,師父不可能那樣講。」於是兩個就跑去找趙州禪師評論。
其中一個說:「師父,您不可能講那樣的話。」禪師說:「你是對的。」
另一個則說:「但我確信您是那樣講的!」禪師說:「你是對的。」
在旁的一位侍者聽了說:「師父,可是他們兩個之中,應該只有一個人是對的啊!」
禪師說:「你說得對。」
(引用自 人生雜誌 FB專頁 ,聖嚴法師美國華盛頓大道堂演講 ,1985年11月。)

這個小故事的典故是:禪宗公案「狗子佛性」。以下引自 佛光大辭典。
禪宗公案名。又作趙州狗子、趙州佛性、趙州有無、趙州無字。
「狗子有無佛性?」自古為禪宗破除執著於有、無之公案。
此係始自趙州從諗禪師,古來即為禪徒難以參破之問答,古德於此多下過慘澹之工夫。
從容錄第十八則(大四八‧二三八中):「僧問趙州: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?』州云:『有。』僧云:『既有,為甚麼卻撞入這箇皮袋?』州云:『為他知而故犯。』又有僧問: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?』州曰:『無。』僧云: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,狗子為什麼卻無?』州云:『為伊有業識在。』」
此則公案中,趙州從諗係藉狗子之佛性以打破學人對於有無之執著。而趙州所指之有無,非為物之有無,乃表超越存在的佛性之實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