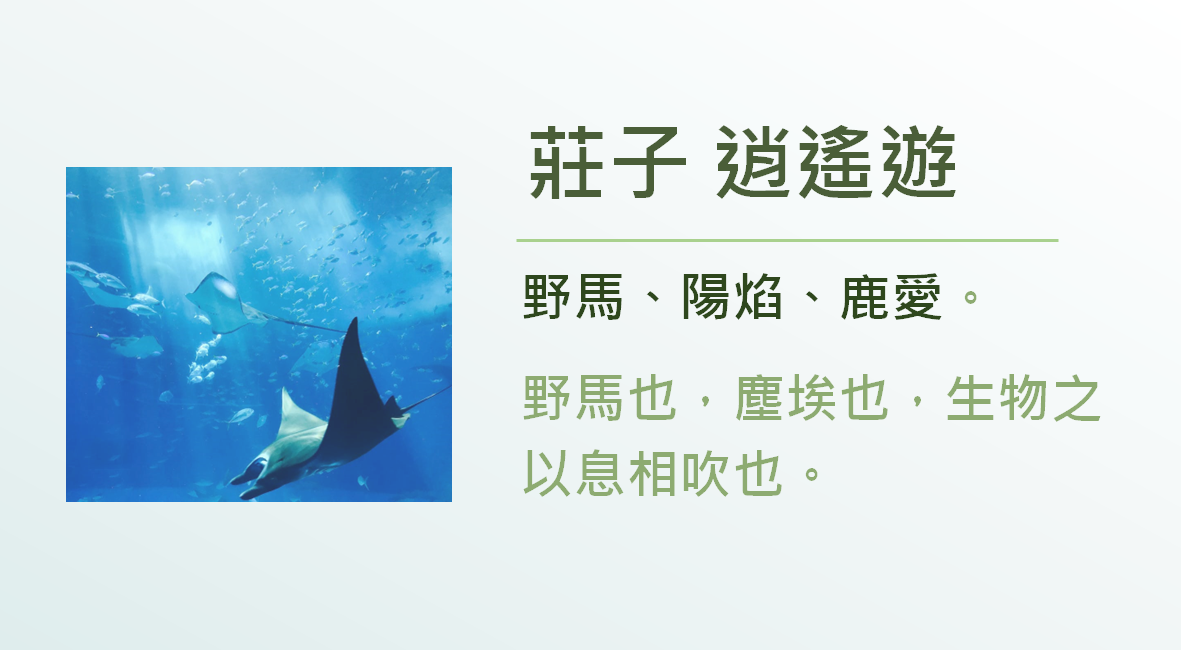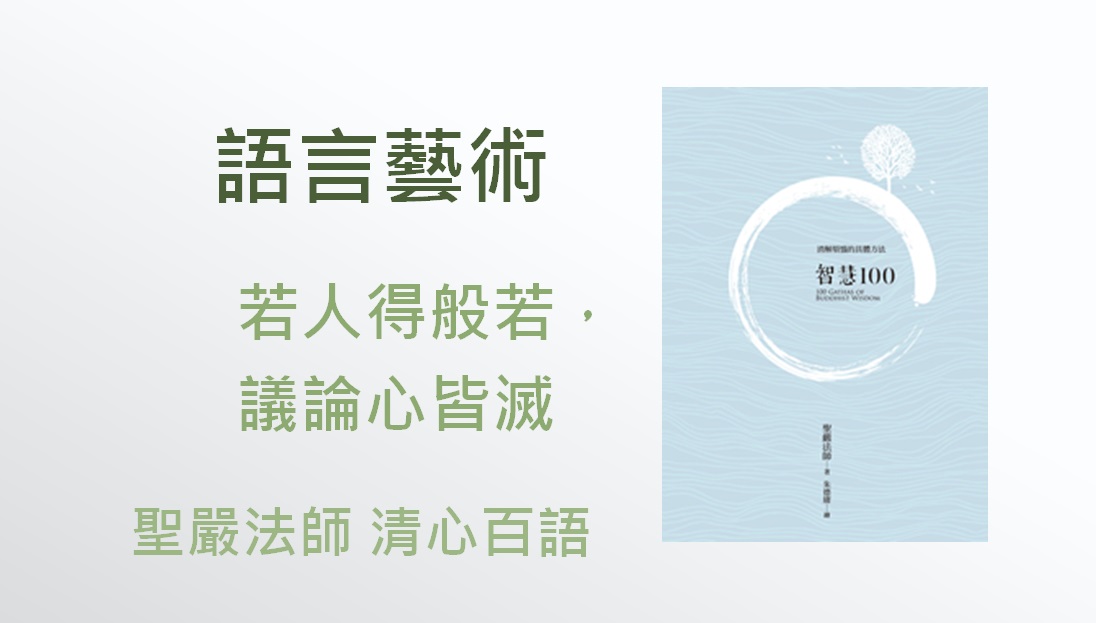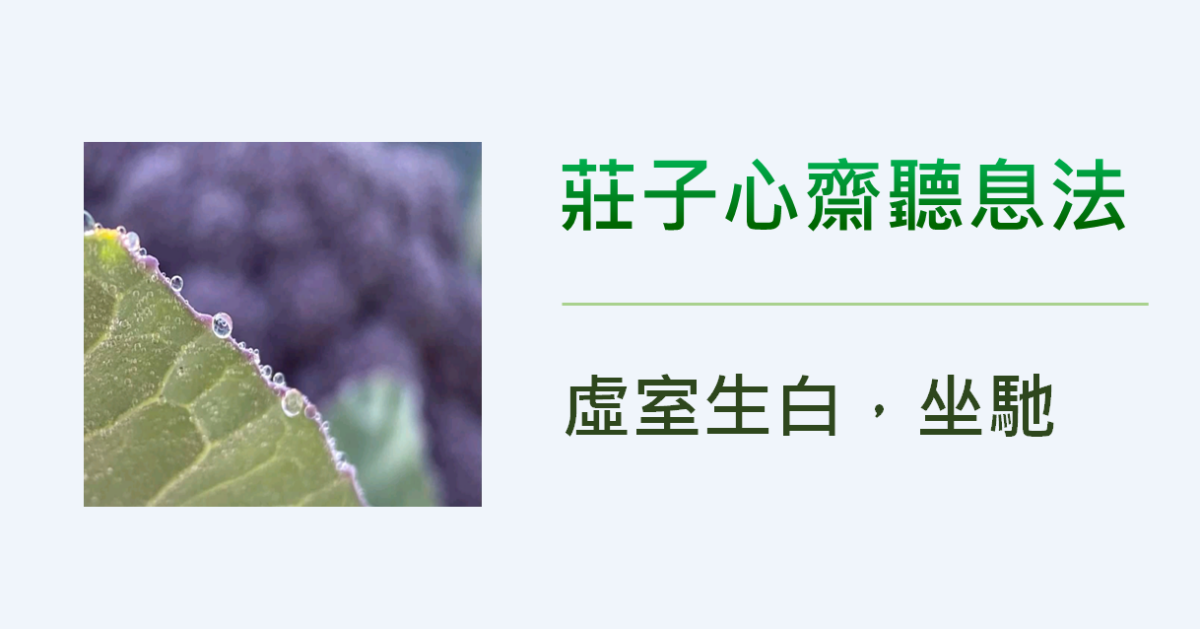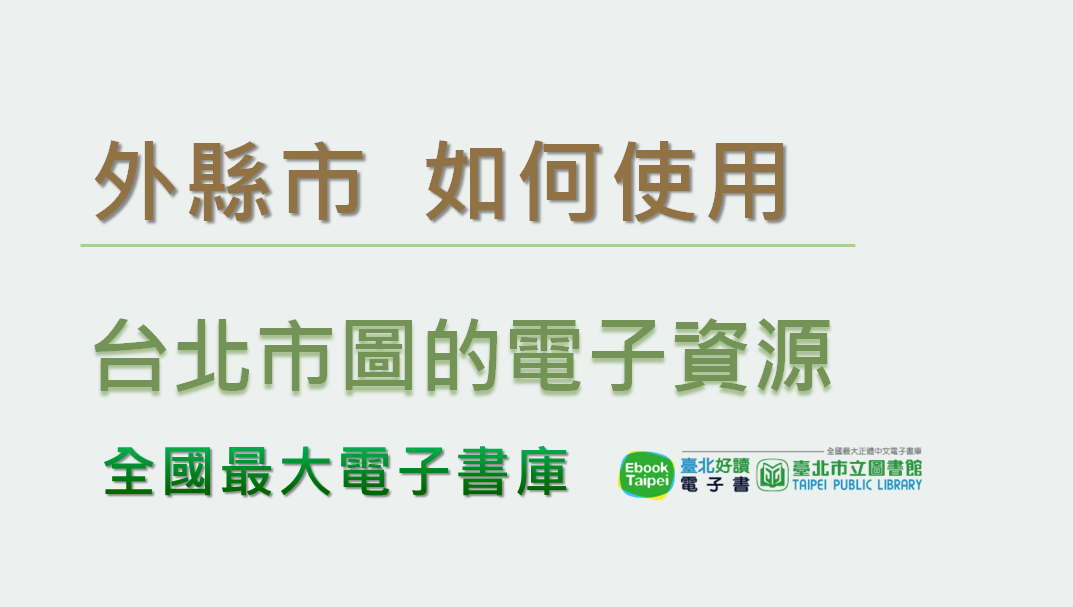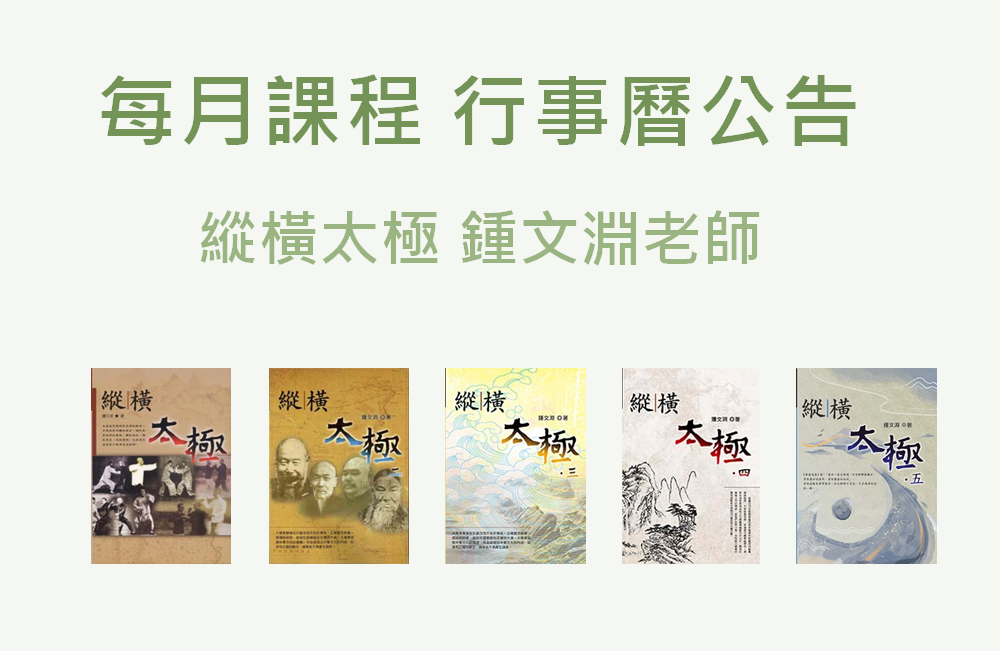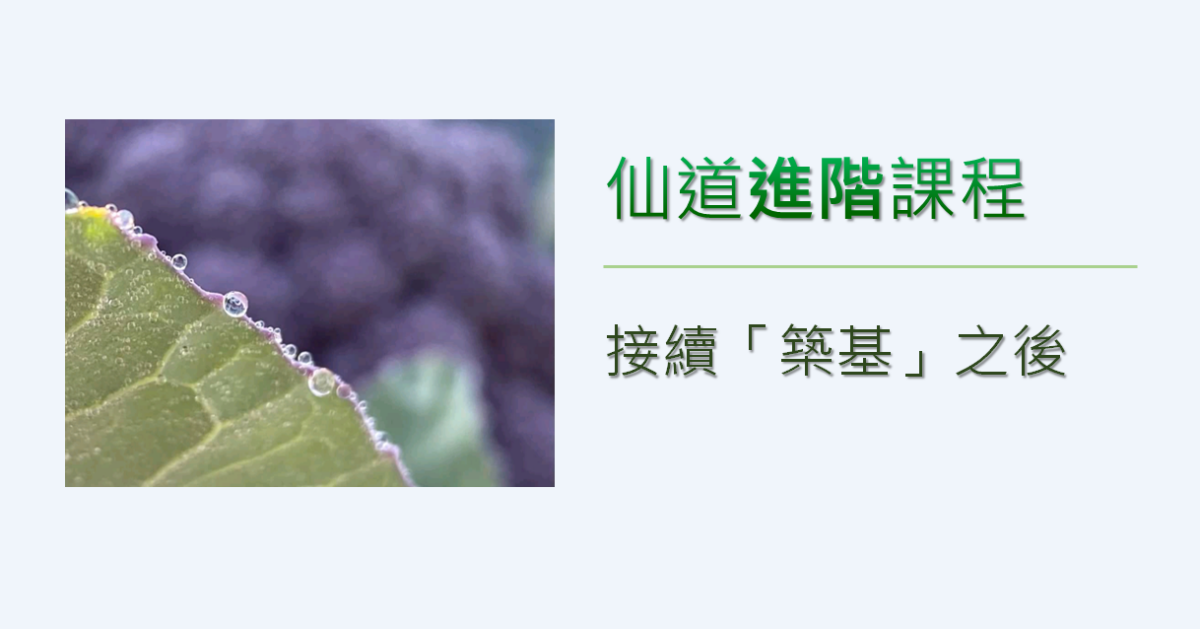莊子《逍遙遊》:
齊諧者,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:「鵬之徙於南冥也,水擊三千里,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,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野馬也,塵埃也,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,其正色邪?其遠而無所至極邪?其視下也,亦若是則已矣。
兩種大氣現象:野馬 、塵埃
這裡的「野馬」、「塵埃,是兩種大氣現象。
「野馬」:指蒸騰的水氣。《莊子》郭象注:「野馬者,游氣也。」,成玄英疏:「此言青春之時,陽氣發動,遙望藪澤之中,猶如奔馬,故謂之野馬也。”」
「塵埃」:則是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。
錢穆《莊子纂箋》:「此言野馬塵埃雖至微,亦有所馮而移動也。」
極微小的水氣、塵埃,都需要有所憑藉才能升騰,何況是大鵬鳥?故須等待到六月,以憑藉大風飛向南方。(且夫水之積也不厚,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,則芥為之舟,置杯焉則膠,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,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,則風斯在下矣,而後乃今培風,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,而後乃今將圖南)。
北宋大科學家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寫到:「莊子言:『野馬也,塵埃也。』乃是兩物。… 野馬乃田間浮氣耳。遠望如群羊,又如水波。佛書謂:『如熱時野馬、陽焰』即此物也。」
以下參考:國科會科普網站-野馬與塵埃:大氣懸浮粒子|科技大觀園
白天地面受日照變熱,近地面的空氣也會因熱傳導而變熱。在氣壓相同時,熱空氣的密度要比冷空氣小,因此產生浮力而上升,而它周遭的空氣因較冷,因而較重,便可能下沉,或者因為暖空氣上升而被迫作出補償性的下沉運動,這便是「自然對流」運動。
很顯然在一個對流中的空氣層,即使是同一高度的空氣密度也不會均勻,而是有的部分密度大,有的密度小。當我們透過這一層對流中的空氣眺望遠方的草原森林時,那些被長草或樹木所散射的陽光進到我們眼睛之前,會先經過這層密度瞬息變化不定的空氣,結果光線的路徑也隨之彎來彎去(這便是折射現象),草原森林的影像一下子對焦,一下子失焦,像是隔著一層翻騰的氣泡。便形成沈括所說的「如群羊」,像一群來回走動的肥羊,又「如水波」的波動,現代名詞稱為「閃爍」。
難道「野馬」與「塵埃」一點關係都沒有嗎?是又不然。「野馬」其實代表著空氣的不穩定性,也正是大氣的不穩定性才能夠支持大量的懸浮塵埃。要是「野馬」不夠「野」,這些塵埃便要紛紛「落定」了,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,野馬與塵埃雖不是同一個東西,卻是緊密關連的。
在佛經亦可見到「野馬」一詞,又作「鹿愛」、「陽焰」,如下幾例。
《禪祕要法經》「如熱時焰,其色正白,如野馬行,映諸不淨。」
教導白骨觀次第修法的《禪祕要法經》卷上:「次教易觀。易觀法者,當更起想念。想念成時,見其身外諸不淨間,周匝四面忽然炎起。如熱時焰,其色正白,如野馬行,映諸不淨。爾時行者見此事已,當大歡喜。以歡喜故,身心輕軟,其心明朗快樂倍常。」佛告阿難:「是名第三慚愧自責觀。」
《出曜經》「當觀水上泡,亦觀幻野馬,如是不觀身,亦不見死王。」
以下引用自釋厚觀法師講解 (福嚴推廣教育班,2016.5.7):應當觀察萬物無常,如同水上的泡沫,也要觀察萬物如陽焰一般虛幻不實,就像是水上的泡沫不會長久存在一樣。
經文翻「野馬」,其實就是「陽焰」的意思,或者是翻成「鹿愛」。陽焰就是日光照到潮濕的地方,蒸發熱氣上升時,現出一種水波的假相,遠遠看好像有水,走近一看,其實並沒有水。所以,在佛典上經常說,鹿看到遠處好像有水,去一看,誒!原來是一種幻相。所以,有的又翻成「鹿愛」,其實就是「陽焰」,有的翻成「野馬」。
《雜阿含經》「觀色如聚沫,受如水上泡,想如春時焰,諸行如芭蕉,諸識法如幻」
以下引自 空海(惟傳)法師:阿含解脫道次第 解說講稿-第八章 五陰
(第十五節)「觀色如聚沫,受如水上泡,想如春時焰,諸行如芭蕉,諸識法如幻」這五句是很簡短,但是大家要背起來,然後慢慢去消化、慢慢去求證。「觀色如聚沫」要慢慢去體會我們身體就像「聚沫」,所謂的「聚沫」,如果在水邊、溪邊沖擊比較久的地區,它旁邊都有一些像海綿,比海綿還更松散那些泡沫、聚沫聚集在一堆,如果用手攪動,馬上破滅掉。所以,我們的身體,事實上就像那些聚沫,看起來好像很結實,但是實在是禁不起碰觸揉捏,現在隨便一個壓縮機把你一擠壓,你就變成肉餅、肉醬。大家不要想說我今天年輕力壯,現在學問高、地位高,無常方面對我來講太遙遠了,如果你這樣太粗心大意,說不定沒多久,你身邊周遭的人,馬上就示現無常給你看,你以為他好好的,結果出去車禍馬上就死掉,人是禁不起一場車禍撞擊的,不要以為說我是鐵打的身體,不怕!像無敵鐵金剛,那個都是夢幻啦!
所以,佛陀就要告訴我們,要去看到身體外表看起來好像很壯健,但是事實上它像聚沫,絕不是消極悲觀,也不是故意誇大,而是佛陀告訴我們實相,要讓我們去看到色身身體就像聚沫,我們種種感受就如「水上泡」,如果有像小瀑布沖刷下來,看到那個水泡一冒上來,然後又很快消失,所以它是冒上來、然後消失,這裡就是宣說我們的種種覺受就是這樣,你的苦受、樂受、喜受,都是這樣升上來,沒多久就消失,升上來、沒多久就消失,只是我們往往會怎幺樣呢?對「樂受」又會想要一直抓住它、不讓它消失;對苦受,我們又希望趕快要設法把它排除掉,不讓它自然的韻律運作,這樣又變成苦上加苦。所以我們要去了解那個實相--觀色如聚沫,受如水上泡,想如春時焰。
所謂「春時焰」,就像在沙漠地區,如果它有一些水氣,然後天氣炎熱,水氣會蒸發,就像一個熒幕出來,如果附近遠方有什幺山景,它會映現出來,因為它在遠處,事實上是水蒸氣蒸發一個幻相的熒幕出來,然後你以為是真的一個世界,叫做「想如春時焰」。國內台中亞哥花園有一個水幕電影,號稱亞洲最大用水做成的一個熒幕,看起來滿立體的,但事實上那些水如果全部都消失,它只是一個夢幻泡影在那裡。所以,有時候你對一件事情,想得很陶醉、很快樂,事實上都是在那裡自我陶醉。所謂「諸行如芭蕉」,「芭蕉」就像香蕉一樣,你一層一層的剝,剝到後面、剝到最後,裡面是「空」,剝到最後裡面就是「空」。所以,你要看到核心的「空」。「諸識法如幻」就像魔術師放一幕電影,讓你看得很歡喜,你以為是真的,結果當它因緣不具足的時候,什幺都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