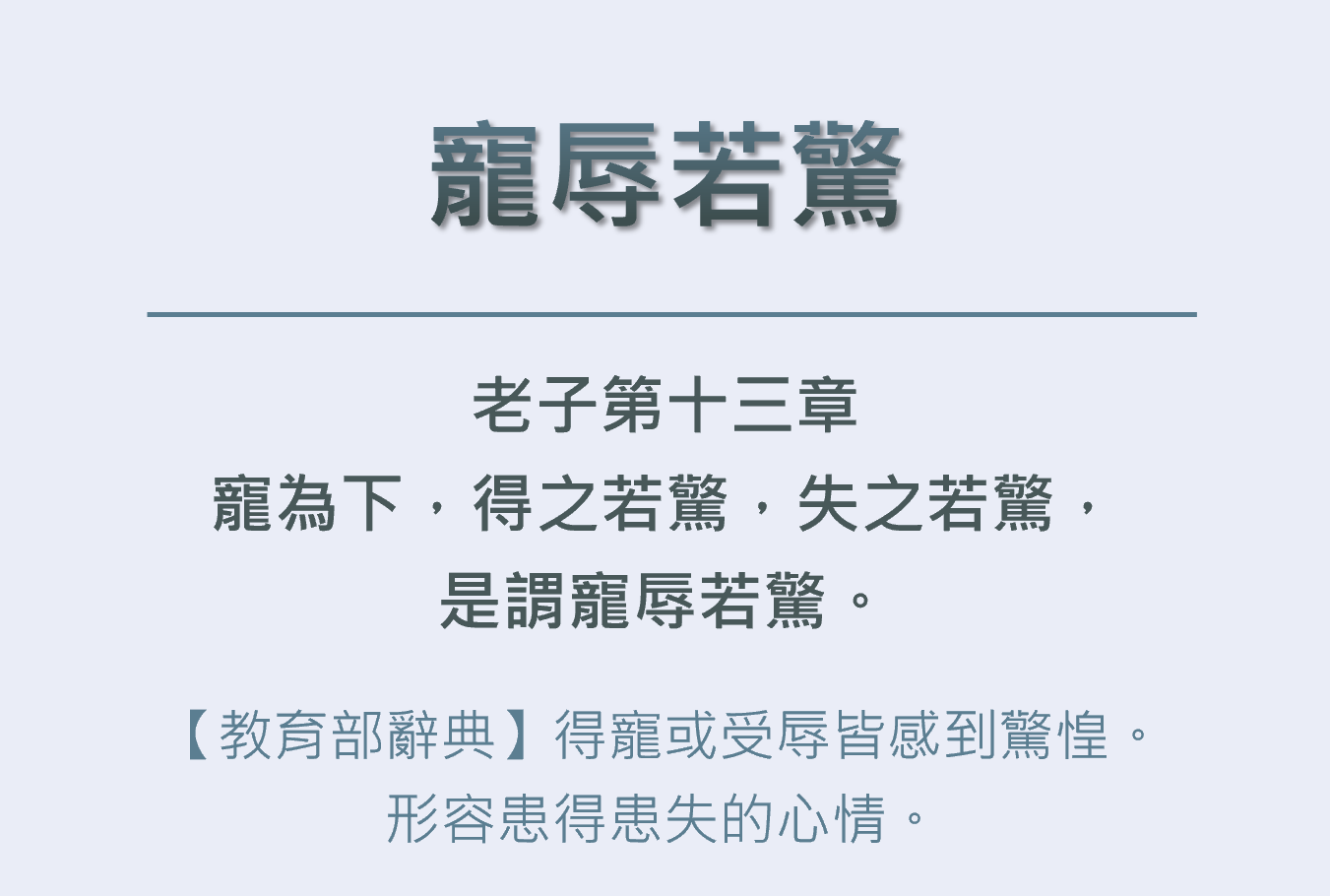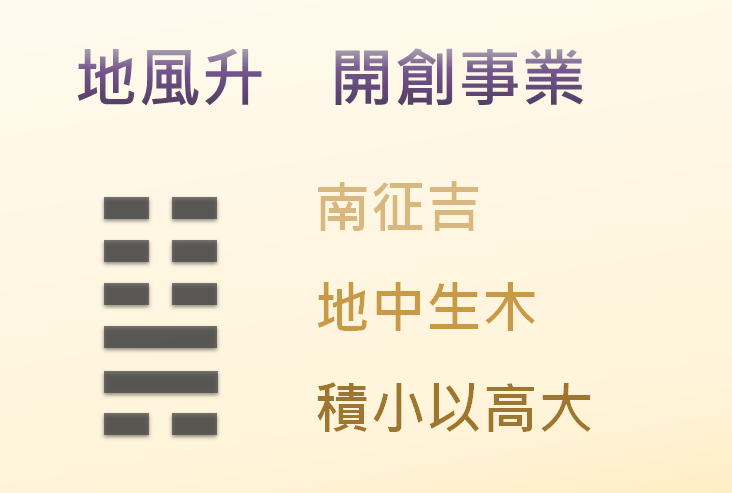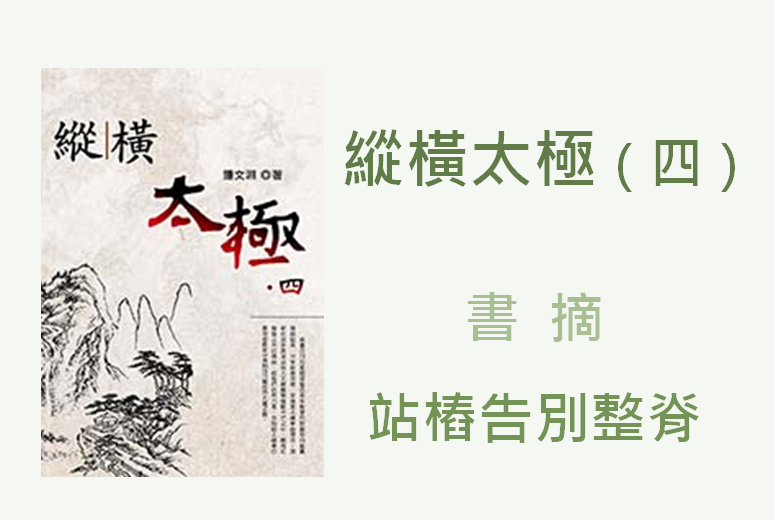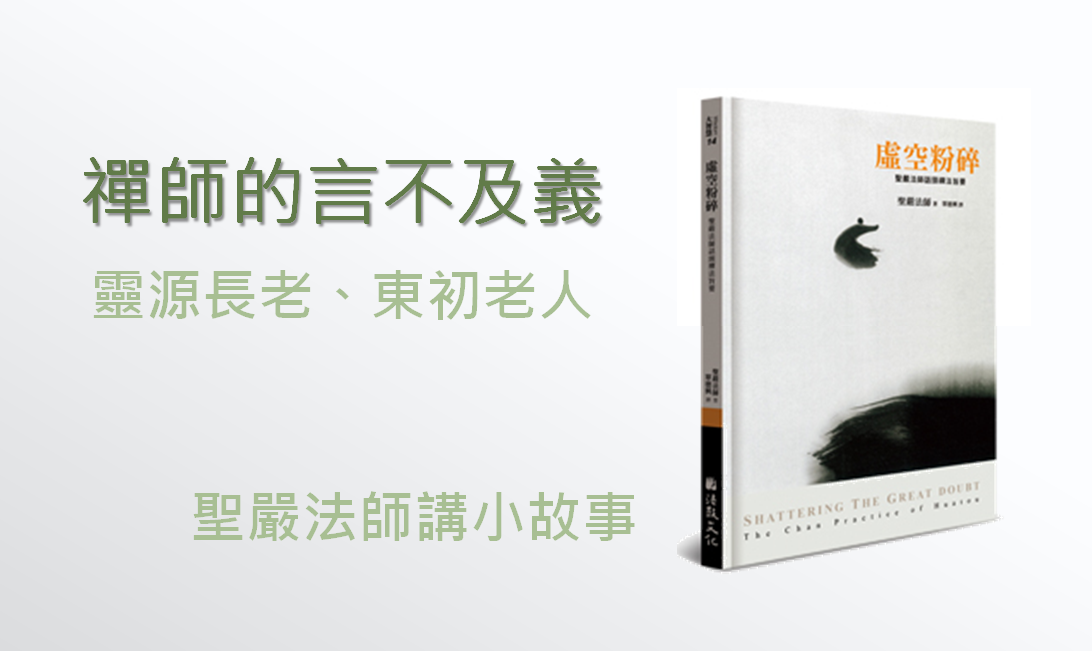阿德勒:個體面對群體的關係
佛洛伊德與其之後的阿德勒、榮格,合稱為「維也納學派」。前幾年曾流行過一系列從日本來的阿德勒心理學暢銷書,例如《被討厭的勇氣》(岸見一郎, 古賀史健,2014,究竟出版社)。
阿德勒的學說,是以自我面對群體的關係來作為立論基礎,他認為人際關係的終極目標是「社會意識」。人類的痛苦既來自於與群體比較,其救贖也是來自於貢獻仁愛於群體,所以這系列書籍在極度重視群體性的日本社會大受歡迎。
這系列看似輕鬆的對話書籍,隱藏了一個根本的立論基礎:我們需要透過與群體他人的關係,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快樂。
阿德勒以「權力欲」取代佛洛伊德的「性欲」作為人的動機,人從小就在家庭裡跟兄弟姐妹比較,社會比較更是自卑來源,需要克服自卑才能獲得成長。
不過老子提出了超越於此的見解。
寵為下
老子道德經十三章:「寵辱若驚,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若驚?寵為下,得之若驚,失之若驚,是謂寵辱若驚。」
為什麼「寵為下」:是誰能給我們「寵」的感覺?是我們心中認為高於我們的人。
我們心中認為比我們低下的人,能提供「尊敬」,但無法提供「恩寵」。
所以當我們因為「得寵」而高興,那麼「屈辱低下」的種子就已經同步埋藏在裡面了。
曾經被抬高過,才會感覺被貶抑
沒有寵,就沒有辱;沒有曾經被抬高過,就不會感覺被貶抑;沒有對比甚麼是光榮尊貴的,就沒有甚麼是卑下屈辱的問題。
再進一步說,這些對比、這些感受,是有賴於其他外在人事物來提供的。
要有一個居於上位的人提供寵愛,我們才感受得寵。
所以無論寵辱,都是受制於人,難道不會患得患失,膽戰心驚嗎?
明星也害怕失去光環
上面說的是從自認低下者的角度來看的,自認尊位者呢?也一樣膽戰心驚。
明星需要粉絲仰慕,皇上需要臣民擁戴,CEO需要部屬聽命,老師需要學生尊敬,網紅需要點擊追蹤。就跟「得寵」一樣,這些仰慕、尊敬、追蹤數,除了心理滿足也連結到實質利益。
離開那個角色時,心生失落,形象落魄;在其位時,對仰慕尊敬一方面沾沾自喜,一方面患得患失。
細思就知道,大家喜愛的這些寵、仰慕、富貴,都是同步埋藏了禍患。有些明星會急流勇退,可能也是不想暴露於大眾眼光,知道寵跟辱是會一起發生的。
不卡在任何角色
這個宇宙是一個整體,寵與辱,光榮與卑下,高與低,貴與賤,都是比較而生的。
如果能消泯那個對比,人跟人相處,隨緣扮演適當角色,但不卡在任何角色上,寵辱不驚,自然就不需要甚麼被討厭的勇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