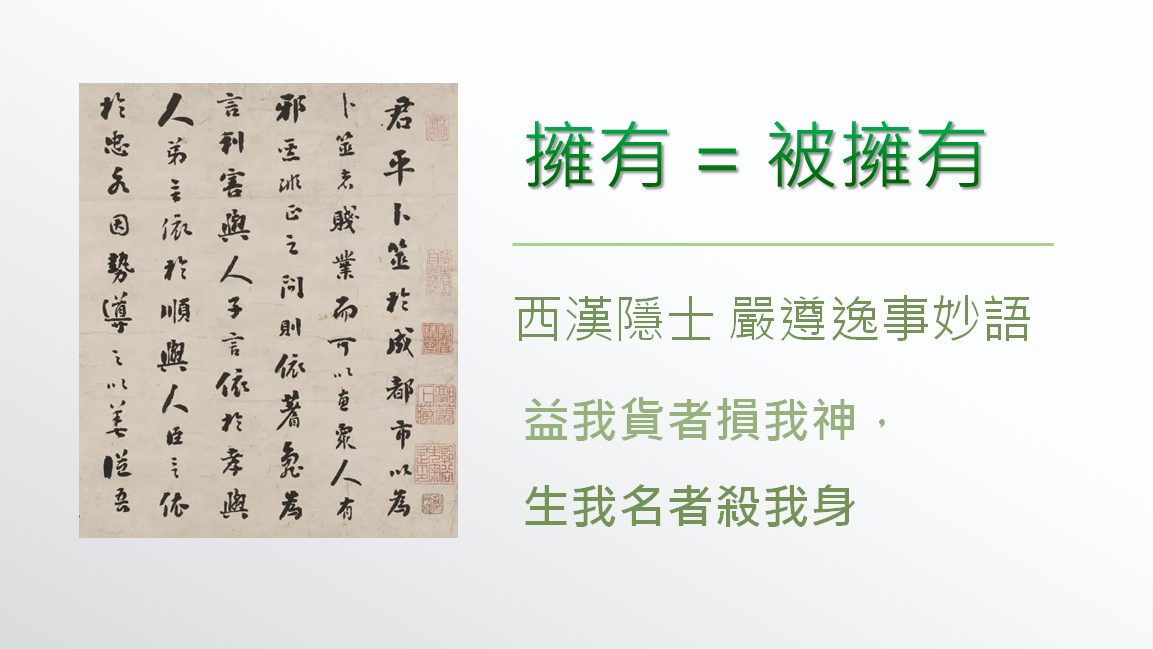根據維基百科:理查費曼在世時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之一。1999年,在英國學術期刊《物理世界》舉辦的130位世界頂尖物理學家參與的票選活動中,費曼躋身十大有史以來最偉大物理學家之列。
自傳《別鬧了,費曼先生》 的中文版序<天才中的小飛俠> 裡面,牟中原說:
為戴森(《全方位的無限》及《宇宙波瀾》作者)評為二十世紀最聰明的科學家,費曼的一生多采多姿,從也沒閒著。他在理論物理上有巨大的貢獻,以量子電動力學上的開拓性理論獲諾貝爾物理獎,在物理界有傳奇性的聲譽。 但他的鮮事也傳頌一時。他愛坐在上空酒吧內做科學研究,當那酒吧以妨礙風化遭到取締時,他上法庭辯護。他的森巴鼓造諧很高,巴西嘉年華會需要領隊貴賓,本來預訂的大明星珍娜露露布麗姬妲缺席,臨時由費曼先生取代,他引以為豪。他一向特立獨行,以不負責任聞名。……. 本書就是費曼一生各種奇異的故事,絕沒有任何說教,也沒什麼深奧難懂的物理學,有的是費曼各種笑鬧鮮事後面,透露出天才的一些天機。
這本書從各種小故事裡,傳達出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人生哲學與研究態度,各個小故事都很有意思。下面節錄兩段,一個是草包族科學,另一段是他這個實事求是的科學家,第一手的被催眠經驗。
草包族科學(Cargo cult science),直譯為「貨物崇拜科學」,利用二次大戰後南太平洋一些土人的行為,來比喻只會模仿外型,卻沒有實質內涵、當然也就不會獲致成效的表面操作。


WIKI:貨物崇拜一詞指二戰期間太平洋某些原住民社會中產生的信仰。他們會建造模仿飛機形狀的模型和形似飛機跑道的設施,期待能夠召喚飛機,像戰爭時代一樣給他們帶來物資。


「草包族科學」(cargo cult science)
摘錄,全文請到《好讀網站:《別鬧了,費曼先生》
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學上的研究,都是屬於我稱之為「草包族科學」(cargo cult science)的最佳例子。
大戰期間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,看到飛機降落在地面,卸下來一包包的好東西,其中一些是送給他們的。往後他們仍然希望能發生同樣的事,於是他們在同樣的地點鋪飛機跑道,兩旁還點上了火,蓋了間小茅屋,派人坐在那裡,頭上綁了兩塊木頭(假裝是耳機)、插了根竹子(假裝是天線),以為這就等於控制塔裡的領航員了——然後他們等待、等待飛機降落。他們被稱為草包族,他們每件事都做對了、一切都十分神似,看來跟戰時沒什麼兩樣;但這行不通:飛機始終沒有降落下來。這是為什麼我叫這類東西為「草包族科學」,因為它們完全學足了科學研究的外表,一切都十分神似,但是事實上它們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——因為飛機始終沒有降落下來。
接下來,按道理我應該告訴你,它們缺乏的是什麼,但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島上的土人說明,是同樣的困難。
你怎麼能夠說服他們應該怎樣重整家園,自力更生地生產財富?這比「告訴他們改進耳機形狀」要困難多了。不過,我還是注意到「草包族科學」的一個通病,那也是我們期望你在學校裡學了這麼多科學之後,已經領悟到的觀念——我們從來沒有公開明確地說那是什麼,卻希望你能從許許多多的科學研究中省悟到。因此,像現在這樣公開的討論它也是蠻有趣的。這就是「科學的品德」了,這是進行科學思考時必須遵守的誠實原則——有點盡力而為的意思在內。
《別鬧了,費曼先生》 (第二部 誤闖普林斯頓 )<自告奮勇>
我們每天穿著日漸褪色的學袍,在那鑲著彩色玻璃窗的大餐廳內吃晚飯。進餐之前,艾森赫院長都會用拉丁文禱告;而在飯後,他也經常會站起來宣佈某些事情。有一個晚上,他說:「再過兩週,一位心理學教授將會來這裡演講催眠術。這位教授覺得實際的催眠示範比單靠討論的效果要好得多,因此他要找些自告奮勇、願意接受催眠的人——」我感到十分興奮:我絕對要深入瞭解催眠是怎麼的一回事。這個機會棒極了!
艾森赫院長接著說,最好有三四個志願者,讓催眠師先試試看誰可以接受催眠;因此,他很鼓勵我們報名參加(天哪!他嘮嘮叨叨的真會浪費時間)!艾森赫院長的座位在大廳的盡頭處,而我則坐在遠遠的另一頭;餐廳裡一共坐了好幾百人。我很焦慮,因為大家都一定很想報名參加,我最害怕的是我坐得這麼偏遠,院長看不到我。但我非得參加這次催眠的示範表演不可!最後艾森赫說:「那麼,我想知道有沒有志願參加的同學——」我立刻舉手,從座位上跳起來,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尖叫:「我啦!我啦!」
他當然聽見了,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叫!那一聲「我」迴盪在偌大的餐廳內,山鳴谷應,使我感到難為情極了。艾森赫院長的立即反應是:「是的,費曼先生,我早就知道你會志願參加。我想知道的是,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學有興趣?」
被催眠的滋味
最後,另外跑出來好幾名志願軍。示範表演的前一週,那位心理系教授跑來找我們作試驗,看看誰是適當的催眠對象。我知道催眠這個現象,但我並不知道被催眠到底滋味如何。他開始拿我做催眠對象,過不多久,我進入了某種狀態,他對我說:「你再不能睜開眼睛了。」
我對自己說:「我敢說我可以睜開眼睛,但我不要破壞現狀,先看看進一步會怎麼樣。」當時的情形很有趣:我只不過有一點迷迷糊糊;雖然如此,我還是很確定眼睛可以睜得開。但由於我沒有睜開眼睛,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,我的眼睛的確睜不開。又玩了很多把戲,最後決定我很符合他的要求。
到了正式示範時,他要我們走到台上,當著普林斯頓研究院的全體同學面前催眠我們。這次的效應比上次強,我猜我已「學會」了如何被催眠。催眠師作出各種示範表演,讓我做了些平常做不到的事;最後還說,當我脫離催眠狀態之後,不會像平常習慣般直接走回座位,而先會繞場一周,再從禮堂的最後方回到座位上。
在整個過程中,我隱隱約約地知道發生什麼事,而且一直都依著催眠師的指示來動作。但這時我決定:「該死的!我受夠了!我偏要直接走回座位上。」
時候到了,我站起身來,走下台階,向我的座位走過去。可是突然一陣煩躁不安的感覺籠罩全身,我覺得很不自在,無法繼續原先的動作,結果乖乖地繞場走了一圈。
後來,我又接受過一名女子的催眠。當我進入催眠狀態之後,她說:「現在我要點一根火柴,把它吹熄,緊接著讓它去碰你的手背,而你不會有任何燒痛的感覺。」
我心裡想:「騙人!不可能的!」她拿了根火柴,點著它,吹熄,立刻把它抵在我手背上,而我只感到一點溫溫的。由於在整個過程中,我的眼睛都是閉上的,因此我想:「這太容易了!她點著這根火柴棒,卻用另一根火柴棒來碰我的手。這沒什麼啦,都是騙人的!」
可是當我從催眠狀態中醒過來後,看看手背,我真的訝異極了——手背上居然燒傷了一塊!後來,傷口還長了水泡,但一直到水泡破掉,始終都沒有感到任何痛楚。
我發現,被催眠的經驗確實非常有趣。在整個過程中,你不停地對自己說:「我當然可以做這、做那,我只是不想那樣做而已!」——那卻等於說:你做不到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