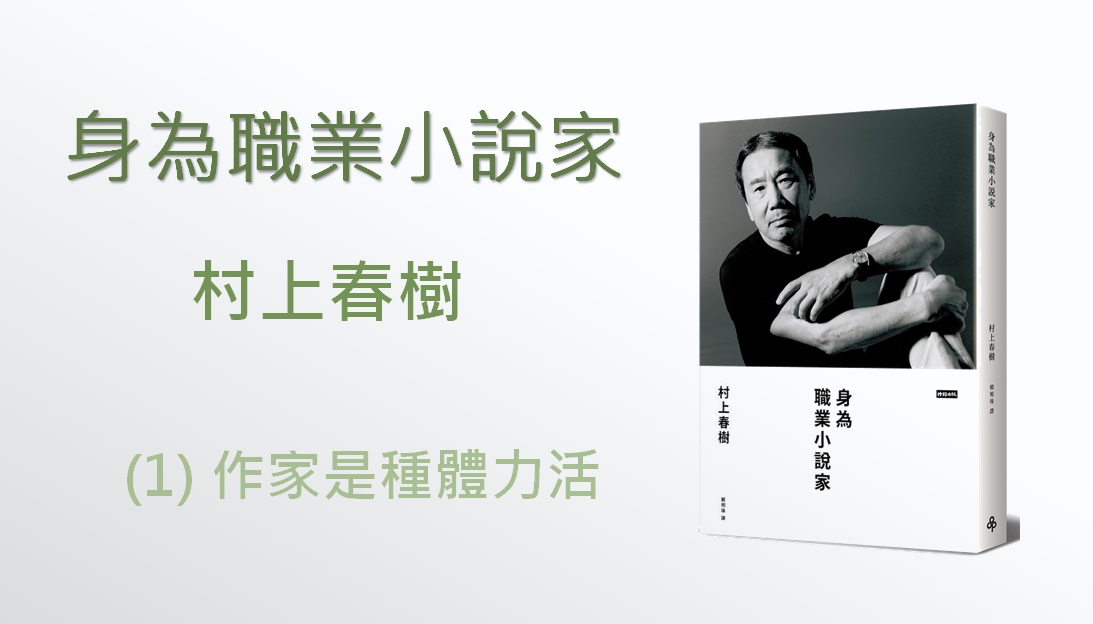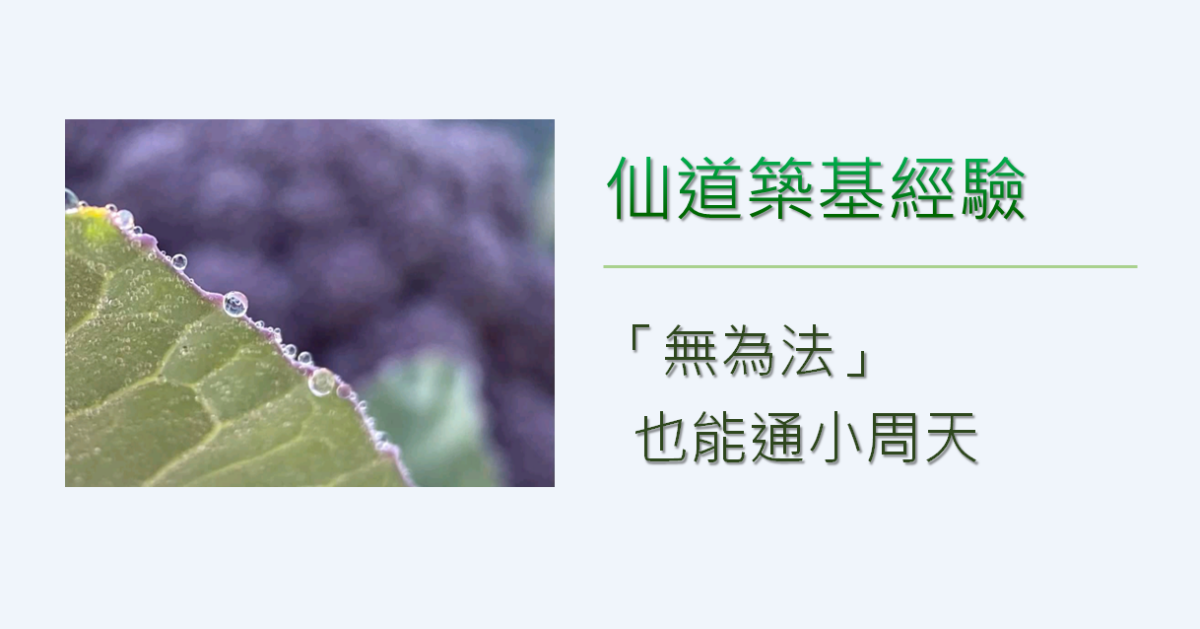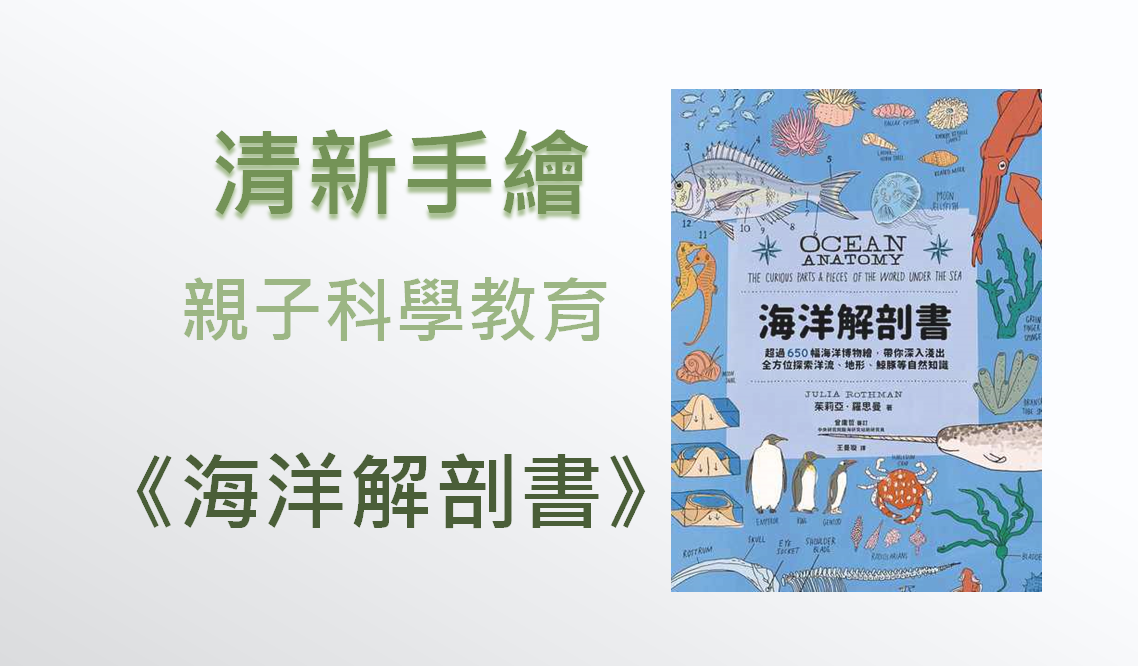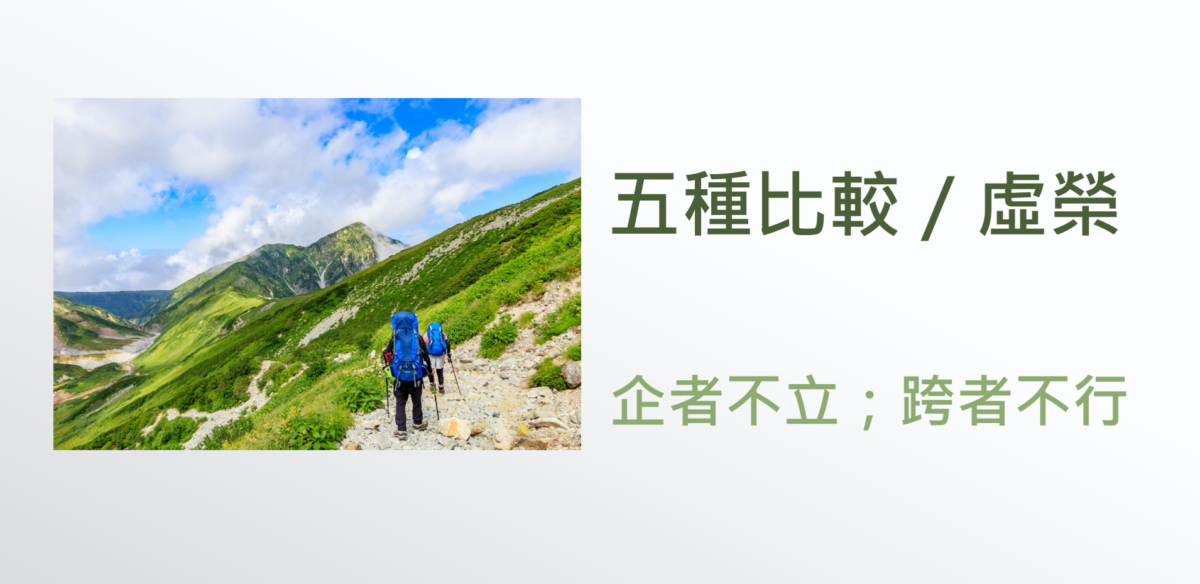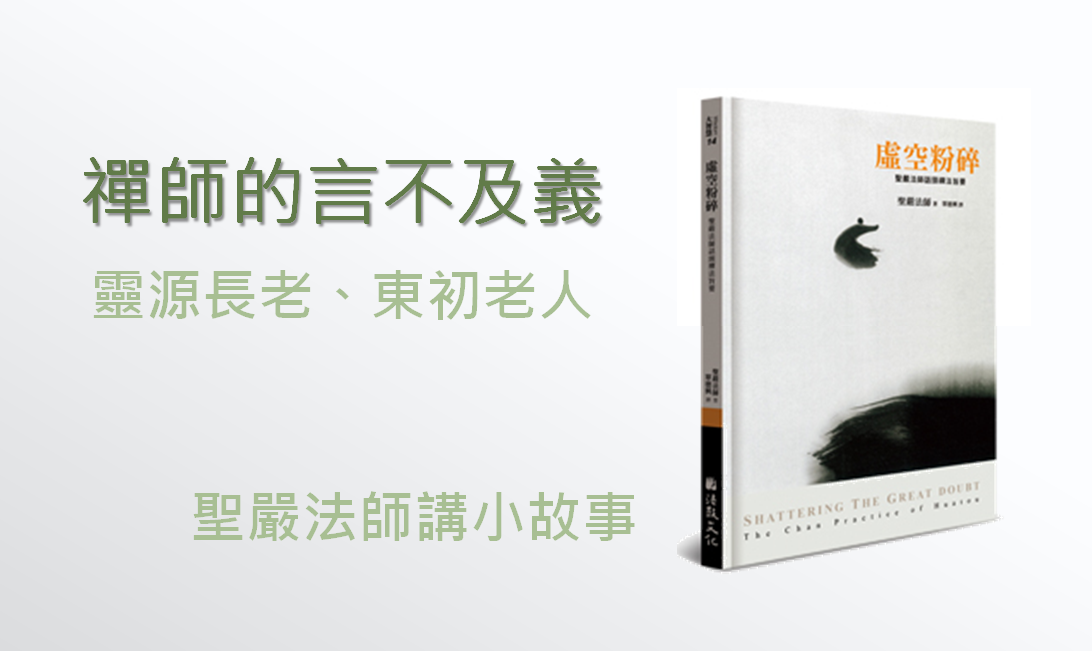共三篇 (1) 作家是種體力活 (2) 精神的實體感 (3) 小說家與精神治療師。請點【村上春樹】
.
對一群讀者說話
這本書與其說是自傳,不如說是作家想和讀者述說的心中話。村上春樹在寫作上,是設定了對一小廳裏約30~40位讀者,流暢而坦率的演講稿。
由於村上春樹在日本很少作公開活動,在超過三十五年的寫作生涯,累積了三代以上的讀者,超出小說成品之外的心情感悟,寄於文字,向長期信賴支持他的讀者,述說這些年來與小說創作有關的點點滴滴。
寫長篇小說:紀律加體力的生產活動
與一般人對作家的浪漫想像相反,寫長篇小說是有實操課表的生產活動,每天需執行規律的作息,定量定時產出固定頁數。他規定自己每天四百字稿紙要寫十頁,想寫更多時,也在十頁左右就停下;覺得不太順時也想辦法寫到十頁,這是因為做長期工作時,規律性具有重要意義。
每天要持續寫作五到六小時,集中意識、構想故事,需要強健的體力。他認為,身體的運動和知性作業的日常性結合,對作家所進行的創造性勞動,能產生理想的影響。所以村上春樹從成為專業作家開始,每天固定跑一小時或游泳,已經持續了三十幾年。
每一階段都需足夠時間:醞釀,成形,「養生」,曝曬,鐵鎚敲打
醞釀,是在自己心中培養出想寫成小說的新芽,讓它茁壯的「沉默期間」。接著以上述的規律生產活動實際寫出來,繼之將成形文字放在抽屜裡慢慢「養生」 。
養生是日文漢字, 有遮蔽保護、養護或固化的涵義。就像工廠製作產品,或建築工地,讓產品和素材只是「熟睡」,放著不動,讓空氣流通,讓內部確實凝固。寫小說也一樣,如果養生沒有做好,會出現生澀乾硬易脆的東西,或組成不均勻的東西。
養生階段之後,拿到外面讓自然光曝曬,意即接受仔細檢查、編輯批評,然後再進入無止盡地細部修改、重複校稿,如同反覆用鐵槌敲打的工作,使盡全力,盡量花很長時間,毫不吝惜地投入所有的能量,可以說是耗盡「總力戰」去戰鬥。
是否有在這些作業的每一個步驟,都一一充分花夠了時間,只有作家本人可以實際感覺到。而且每一步驟所花時間的品質,一定會影響到最終成品的「認可度」,也就是會產生出截然不同的體感。
什麼?體感?文字怎麼會有身體觸感呢?這在下一篇 《(2) 精神的實體感》會做說明。
.


《身為職業小說家》書摘
( 我的學生時代大約在一九五○年代後半到一九六○年代之間,當時校園霸凌和中輟生的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。並非學校和教育制度沒有問題(我認為有不少問題),至少以我自己來說,身邊幾乎沒有看到霸凌或拒絕上學的例子。雖然還是偶有發生,不過並不嚴重。
在戰後不久的年代裡,國家整體還比較貧窮,我想可能是因為有「復興」「發展」之類明確目標在運作的關係吧。就算隱含了問題和矛盾,基本上還是擁有積極正面的空氣。這種周圍的「方向性」般的東西,可能也在孩子們之間產生了眼睛看不見的作用。我想在孩子們的日常生活裡,世間似乎並不存在擁有巨大負面能量的事情。基本上反而抱持著「如果這樣努力的話,周圍的問題和矛盾不久自然會消失」的樂觀想法。因此我雖然也不太喜歡學校,但因為「上學是理所當然的」,因此未曾質疑過,就滿認真地去上學。
不過,今日霸凌和中輟生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,報紙、雜誌和電視報導,幾乎沒有一天不提到。部分受到欺負的學生甚至自殺。除了悲劇之外真的沒有別的說法。針對這種問題人人都有各種意見,社會也採取種種對策,但完全看不到問題有減輕的傾向。
不只是同學之間互相欺負而已。教師方面的問題也不少。在有一段時間之前,神戶有一所學校,隨著開始上課的鈴聲響起,老師會把沉重的校門關上,結果造成一個女學生當場被夾死的事件。老師辯解說是因為「最近遲到的學生太多,不得不這樣做」。遲到當然不可取。但學校遲到幾分鐘,和一個人的生命哪一邊價值比較重,這是不用考慮的事。
在這名老師心中「遲到不可原諒」,如此狹隘的意識在腦子裡異樣地膨脹,導致無法保持平衡看世界的良好視野。平衡的感覺對教育者來說應該是重要的資質。報紙上也刊登家長的意見,「那位老師是熱心教育的好老師」。可是說出這種話──說得出的一方似乎也有問題。被殺的一方,被壓碎的疼痛到底要向誰述說發洩?
比喻上說學校壓死學生,不難想像是怎麼回事,實際上真的讓學生活活被壓死的學校,就遠遠超越我所能想像的了。
像這般教育現場的病症(我想可以這樣說),不用說,就是社會體制的病症的投影,無庸置疑。如果社會全體擁有自然的氣勢,有確定的目標的話,就算教育體制多少有一點問題,也總能以「場所的力量」適度調整度過。但是當社會失去氣勢,在很多地方產生閉塞感時,其中情況最明顯,受到波及作用最強的就是教育現場。是學校,是教室。因為孩子們,就像礦坑裡的金絲雀一樣,最先感覺到那汙濁的空氣,是最敏感的存在。
就像剛才說過的那樣,當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,社會本身有「伸縮性」。因此類似個人與制度對立的問題,也被那伸縮空間吸收進去,沒有造成多大的社會問題。因為社會整體在動著,那動力把各種矛盾、挫折和不滿都吞進去了。換句話說,傷腦筋的時候,到處都有很多可以逃進去的餘地或空隙之類的地方。但到了高度成長時代結束,泡沫時代也結束的今天,很難再找到這種避難空間。過去只要順著大潮流走就會沒事,那種大體上籠統的解決方法已經不成立了。
伴隨這種「可逃場所不足」的社會教育現場的嚴重問題,我們有必要設法找到新的解決方法。或者,照順序來說,首先必須在某個地方成立可能發現全新解套方法的場所。
個人回復空間
那是什麼樣的場所?
個人和體制可以自由地相互活動,一邊安穩地協商一邊能找到對雙方最有效接觸的場所。換句話說,是每個人在那裡都可以自由伸展手腳,慢慢呼吸的空間。能夠脫離制度、階級、效率、霸凌之類事情的地方。簡單說,是個溫暖的、暫時性的避難場所。誰都可以自由進入,可以自由地從那裡出來。不用說那是屬於「個人」和「共同體」的中間地帶的場所。想要在哪一帶找位子,都依每一個人的意思決定。總之我想稱這個場所為「個人回復空間」。
剛開始只要小空間就可以。不必大規模。即使在手作般的狹小場所,總之各種可能性都實際試著去做看看,如果順利的話,就可以那個為模式=基礎方案,繼續發展下去。我想空間可以逐漸擴大。雖然某種程度需要花時間,但我想那可能是最正確,最合理的做法。我想這種場所如果能在各種地方自然產生該有多好。
最壞的情況,是從文科省之類的地方由上而下設定一種制度,然後把那種東西硬推給教育現場。我們在這裡是以「回復個體」為訴求,如果國家準備以制度化來解決的話,可以說真是本末倒置,或者搞不好可能成為一種鬧劇。
閱讀是一所「客製化」學校書摘
雖然談的是我個人的經驗,不過現在回想起來,對上學時代的我來說,最大的救贖,我想是在那裡交到幾個好朋友,還有讀了很多書。
關於讀書,總之我真的拿起眼睛看到、各種各類的書,像往燃燒正旺的窯裡用鏟子送煤進去般,貪婪地讀下去。每天為了品嘗、消化那一本一本讀物就忙不完了(雖然很多也消化不了),幾乎是處於沒有多餘時間去考慮其他事情的狀態。我也想過,那對我來說或許反而是一件好事。如果我好好看清自己周圍的狀況,認真考慮那裡所存在的不自然、矛盾和欺瞞,對不認同的事情直接追究到底的話,或許會被逼進死胡同般的地方,弄得灰頭土臉也不一定。
於是,由於讀遍了各種各類的書,視野自然某種程度「相對化」了,對十幾歲的我來說,我想是具有很大意義的。由於書中所描寫的各式各樣的感情幾乎都作為自己的東西般體驗,在想像中自由地穿梭在時間與空間之間,目睹各色各樣不可思議的風景,讓各種語言通過自己的身體,因此我的觀點或多或少變成複合性的。也就是現在不只是從自己所站的地點眺望世界,變成也能從稍微離開的其他地點,適度客觀地眺望正在眺望世界的自己的身影了。
只從自己的觀點眺望事物時,世界無論如何都會咕滋咕滋地將水分蒸發漸漸煮乾。身體變僵硬、腳步變沉重,變得無法自由轉身。但如果能以幾個觀點眺望自己所站的位置時,換句話說,自己的存在如果能託付到某個別的體系時,世界便開始變得比較立體,和比較帶有彈性。我想,這應該是人活在這個世界上,意義非凡的姿態。透過閱讀學到這個,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收穫。
如果沒有書這東西的話,如果沒有讀這麼多書的話,我的人生應該會變得比現在寒冷而殺風景,僵硬而死板。換句話說,對我來說讀書這行為,本身就是一個大學校。那是為我而興建並營運的,特別訂做的學校。我在那裡親自學到許多重要的事情。那裡沒有麻煩的規則,沒有靠數字評價的事,沒有激烈的名次之爭。當然也沒有霸凌之類的事情。我雖然被包含在很大的「制度」之中,但也能好好確保那另一個屬於自己的「制度」。